他謙卑而傲慢,立身維小而為鈞維大;他的陶瓷,龐雜而至簡,婉約而至定,傳統而時尚;他是鈞瓷界的“異類”,甚至是鈞瓷的“叛徒”,但他創燒的鈞瓷道玄缽,被通古今中國陶瓷之變的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耿寶昌先生譽為“劃時代的作品”。
他,就是劉家鈞窯掌門人劉建軍。
在神垕乃至禹州,關乎劉建軍,可謂毀譽參半。譽者贊其為“立德,立言,立行”的楷模,是“大師中的大家”;毀者蔑其為手緊而吝嗇,是鈞瓷的“異類”。
毀譽之評,往往全是對劉建軍的德性與為人的“審判”。當面對其陶瓷作品時,無論毀者、譽者,往往都會豎起大拇指,贊譽有加。也因此,他成了鈞瓷界獲獎專業戶。論獎項之高之多,罕有匹敵。
也許譽者“潛伏”某種期許,毀者“夾雜”某種祈望。在鈞瓷界,劉建軍是個“人物”,不言而喻。也許,他們都寄望劉建軍能夠頂天立地。
劉建軍的鈞瓷,大都是瓶瓶罐罐,偶爾間雜一些夸張變形的“流行鈞瓷”,做工精微,都是不壞的瓷器。仔細觀察,能夠發現其鈞瓷的好;放眼一觀,其鈞瓷還難以跳出禹州鈞瓷的當下固巢。
一件外黃內青的鈞缽似乎改變了這當下的“固巢”,“道玄缽”可謂至美、至純、至簡、至定的新品。據鈞瓷鑒賞家王豐碩介紹,這個“道玄缽”,徐光春書記(河南省委前書記)憐愛有加,耿寶昌先生稱之為“劃時代的作品”。
一件鈞瓷,能讓內行、外行都去憐愛,自然就是一件好的鈞瓷。通曉古今中國陶瓷之變的耿寶昌先生贊其為“劃時代的作品”,不是奉承之辭,恰恰切中肯綮。無論哪個領域,“劃時代”者總是不凡之才。劉建軍自有不凡的學藝歷程和天賦。
1952年劉建軍出生在神垕的鈞瓷世家。“父親劉振海是禹縣(禹州)鈞瓷二廠技術副廠長,七級工,拿64.25元的工資,在廠里領的是最高工資。”劉建軍說,“但那時‘七級工,八級工,趕不上社員一溝蔥’——加上我們兄妹五人,一家7口,自然過得異常寒苦,住在一間20平方米的房子。床底下都是人,晚上解手,都是邁過這個,還有那個。”
其實,家里住房緊張,劉建軍從小都喜歡到街上去“混”,到父親的廠里去玩。“看得多了,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學著用泥捏毛主席像章、用電爐烤毛主席像章。”劉建軍說,“1968年,剛滿16歲,初中畢業,就進了父親所在的鈞瓷二廠。”起初,他在實驗室搞高壓電瓷實驗:“惡補陶瓷工藝美學,最后實驗成功了,燒成了高壓電瓷,但還是搞不懂到底怎樣弄成的。”1972年,禹縣(禹州)各大瓷廠已經開始研制、恢復鈞瓷生產,劉建軍渴望父親能讓他到實驗室搞鈞瓷的造型與釉色研究。但是,父親卻硬要他燒窯。燒窯,苦不堪言。一窯燒下來,二三十個小時;每隔15分鐘,添煤一次,又臟又累又苦。
開始燒窯,劉建軍創下了連燒17窯的失敗記錄。無奈,他只好從頭學習。他到盧振興那兒,看了一個星期;他到劉國安那兒,又看了一個星期。學習盧振興、劉國安的經驗,結合自己的情況,劉建軍邁過了燒窯這道坎兒。這窯,一燒就是8年。直到1980年,劉建軍調任二廠技術科擔任副科長,負責釉面磚研究;1983年扶正,成為技術科科長。
“其實,‘寒鴉歸林’掛盤是1974年燒出來的。燒成后,就扔到了倉庫里。直到1983年二廠要在中國工藝美術館搞展覽,這才想起了那個掛盤。”劉建軍說,“幾個人費了很大的勁才扒了出來,看來看去,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巧奪天工’。姚雪垠先生一聽,就笑了:‘太土,太沒詩意,明天我給它起個名字’。第二天,姚先生送來一首詩:‘出窯一幅元人畫,落葉寒林返暮鴉。晚靄微茫潭影靜,殘陽一抹淡流霞。’這才有了‘寒鴉歸林’。”
“‘寒鴉歸林’,那是碰的,根本不知道是如何燒出來的。它的揚名,也與時代密不可分。”劉建軍淡淡地說。
1984年年底,劉建軍升任鈞瓷二廠技術副廠長;1991年5月,調任鈞瓷一廠廠長兼黨委書記;1993年,劉建軍辭職并于次年與弟弟劉志軍共創“建軍鈞窯”;2005年,“建軍鈞窯”更名為“劉家鈞窯”。
劉建軍陶藝生涯近40年,陶瓷藝術成就卓爾不群,卻也兩次與“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擦肩而過。1988年,第四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選,鈞瓷界推選的是鈞瓷一廠時任廠長劉國安、鈞瓷二廠時任技術副廠長劉建軍。但是,評選制度要求擔任領導職務者不得參選。于是,鈞瓷二廠推薦了邢國政、鈞瓷一廠推薦了劉富安。因為名額只有一個,邢國政已經退休,劉富安當選為鈞瓷界的首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2006年,第五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選,劉建軍與孔相卿、任星航、楊志被推舉為候選人,最后孔相卿、楊志當選,劉建軍再次落選。是年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委范文典先生事后對劉建軍說:“你報送的評選作品,包括鈞瓷、汝瓷、官瓷、哥瓷,評委不知如何將你歸類,這可能是你落選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燒鈞、汝、官、哥,說不為了掙錢,是笑話;說完全為了掙錢,也不是實話。”劉建軍說,“鈞、汝、官、哥、定是宋代五大官窯,其中鈞、汝、官、哥都在青瓷一系,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是顯而易見的。為燒好鈞瓷,我必須研究汝、官、哥,燒好汝、官、哥呀!”
路就在腳下。3年后,劉建軍厚積薄發,“道玄缽”——“劃時代”的“道玄缽”終于君臨天下。如果沒有鈞、汝、官、哥四窯同燒,“劃時代”的“道玄缽”不可能誕生。回首而望,方知天道酬勤:四窯同燒是一座必然要過的橋梁,不在這座橋梁上艱苦它化,就不會有“道玄缽”的悄然自化。
釉變而型變
什么鈞瓷才是好鈞瓷?身為禹州人,我只能說看著順眼就留著吧。
今天,又面對一個賀歲鈞瓷的新品,劉家鈞窯推出的《虎福吉祥》。作品的意蘊,顧名思義即可。我感興趣的,倒是那奇特的“金質開片”施釉工藝。
在禹州召開的2009年中國鈞瓷文化旅游節上,劉家鈞窯推出的道玄缽使人驚艷不已:半球狀的造型不足為奇,奇就奇在鈞釉展現在缽的內側,明凈的天藍色;而外圍卻是一種暗黃的厚釉,看起來茸茸的,摸起來澀澀的,似柔還剛。像皸裂的河床嗎?像秋后的大地嗎?
似是而非,承道載玄。鈞瓷可以這樣做嗎?可以!它贏得了大家的好評。這還是鈞瓷嗎?應該是吧!但它換上了另一件時裝。“要傳承鈞瓷藝術,就要不斷賦予它新的內涵。”道玄缽的制作者、劉家鈞窯掌門人劉建軍如是說。
同樣對鈞瓷過目不忘的經歷,還有兩次。一次,是在北京韓美林工作室。見到一些韓先生設計、監造的鈞瓷作品。獨特的裝飾風格、碩大的形體,使人感受著韓氏造型的磅礴大氣。最讓我難忘的是上面厚重的鈞釉,像火山巖漿,好像要流動的樣子;像潑彩的山水,云霞滿眼。
鈞釉可以這樣做嗎?應該可以,就在我的面前,如此壯麗。韓氏風格的作品現已很常見,成為鈞瓷史上難以回避的一頁。韓美林應該感謝鈞瓷,這種獨到的工藝方法,讓他找到了更廣闊的揮灑靈感的空間。鈞瓷也應該感謝韓美林,獲得大師級的助力,姿態百生。
又一次是在海南博鰲,2003年的冬天。由榮昌鈞瓷坊制作的《祥瑞瓶》作為國禮贈與各國政要。對于鈞瓷來說,《祥瑞瓶》展示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鮮——匯集眾多大師智慧的創意、以國禮的形式成批次亮相、申請國家專利、限量制作和一場又一場的發布會……這一切,開啟了鈞瓷制作營銷的新時代。
鈞瓷可以這樣做嗎?多年來,鈞瓷振興的事實,就是最好的答案。
2005年,在鈞瓷《華夏瓶》開窯儀式上,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說,選擇鈞瓷作為國禮,不僅僅因為它是具有千年歷史的宋代五大名瓷之一,更重要的是其厚重的歷史文化和瑰麗豐富的窯變神韻,從某種意義上表達了古老的中國在復雜多變的多極化國際環境中,所堅持的中國文化的渾厚質樸和與時俱進的積極應變態度。
應變,是時代精神的核心,也是鈞瓷振興的源泉。只有變化,才能出新;只有變化,才能傳承;只有變化,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使人過目難忘。冠以珍品名號的鈞瓷太多了,但讓人過目難忘的鈞瓷,才是真正的珍品。
改革開放后,盡管劉富安、晉佩章、苗錫錦、孔相卿、劉建軍、楊志、任星航、王金合、苗長強、晉曉瞳等,對鈞瓷的向前發展都有過不凡的貢獻,但是對鈞瓷發展真正形成強烈“沖擊波”的,其一無疑是韓美林的“器型之變”,其二無疑是榮昌鈞瓷的“營銷之變”。
韓美林要打倒“解放鈞”、苗峰偉要搬倒“紅瓶子”——他們直指“釉變”,企望“釉變”,但都沒有直抵彼岸。“器型之變”、“營銷之變”后,“釉色之變”成為時代的課題。
劉建軍的“釉變”贏得一片掌聲,已然給出了一個鈞瓷“釉變”方法或方向。“釉變”之時,劉建軍也在探索“器變”。至少,《虎福吉祥》上的老虎,溫柔得如一朵牡丹花,《事事如意》則“勇敢”地站了起來。劉建軍的“釉變”而“型變”,是繼韓美林“器型之變”、榮昌鈞瓷“營銷之變”后,正在聚集而為鈞瓷的第三“沖擊波”。
鈞瓷,只有窯變是不夠的。還需要“器型之變”、“營銷之變”、“釉色之變”……劉建軍還在路上,祈望他在道玄缽劃了時代后,進而在鈞瓷發展史上寫下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 (編輯:木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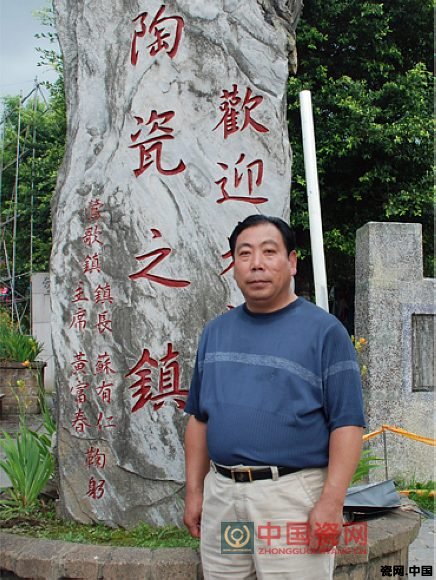
鈞瓷工藝大師劉建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