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資深藏家、鑒賞家李廣琪是在端午小長假結束后的上班首日,外面下著雨,大約在上午10點30分,他趕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陽區的亮馬國際珠寶古玩城。乘 坐扶梯來到三樓,左手邊第三家蘭祺軒就是他的古玩店。里面陳設很有講究,寶貝更是包羅萬象。看著大家參觀他的蘭祺軒,李廣琪直言不諱地告訴大家哪些是新貨、哪些是舊貨。
雖然僅僅是第一面,但是談吐間,看得出李廣琪不但古玩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為人也很實在。此前,李廣琪的大名早有耳聞,坊間稱之為“仿古高手”,行內人拜其為鑒定專家,媒體人則稱之為“仿古泰斗”。就在采訪中,對面一位古玩店老板物色到一個寶貝,讓店員 小心翼翼地拿給李廣琪看看是不是真貨。“李老師,這是剛快遞過來的,花了4000元淘的老貨。”店員話音剛落,李廣琪直言“假的,這是新貨!”順便叮囑, “看看能不能退,不能退就當交學費了!”
古玩商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只要他們聊起古玩,亮出寶貝,你就會發現,這些人實在非比尋常。李廣琪就是這樣一位資深玩家。
談到古玩行業,李廣琪算是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步入這個行業的玩家。在他的記憶中,文化大革命是殘酷的,對幾千年的文物更是發動了滅絕性的打擊。言談間,他充滿了遺憾和惋惜。10年之間,這個古國變成了一片極其蒼白乏味的土地。“破四舊”運動席卷全國,只要沾上“老舊”的東西,要么查抄,要么焚毀,要么砸爛和破壞,誰家里也不敢擺放老物件,更別說公開談論、收藏了。由于佛像是四舊,全部拉到銅廠化成銅,瓷器都砸了,字畫也都燒了。因而市場上木器、家具剩下的多一些,至于瓷器、銅佛像幾乎都是零。文物市場也隨之邁入了零時代。用他的話說,“那個時候,黃金珠寶就堆在那里,誰敢碰?大家都避之不及。”10年后,一些社會邊緣人盤踞于城市一角,兜售著瓷器碎片,盡管在很多人眼中這只是一堆破爛,但卻有那么一些人執著于它們的出處、工藝和歷史,那個時候又能有多少人知道,這些別人瞧不上眼的瓷器碎片,卻是了解瓷器收藏的“活標本”,可以稱得上是“碎寶”。有行內人打了這樣一個經典的比喻:“這些碎瓷片就像大家家里用的開水瓶,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征,早期是竹子外殼的,后來是鐵的,也有的是塑料的。文物也是同理,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征,完整的瓷器雖已不在,但它的精美工藝卻在瓷片上保留了下來。”所以他們不是在簡單地兜售一些破碎的瓷片,而是在推動這些碎片發展成文化復蘇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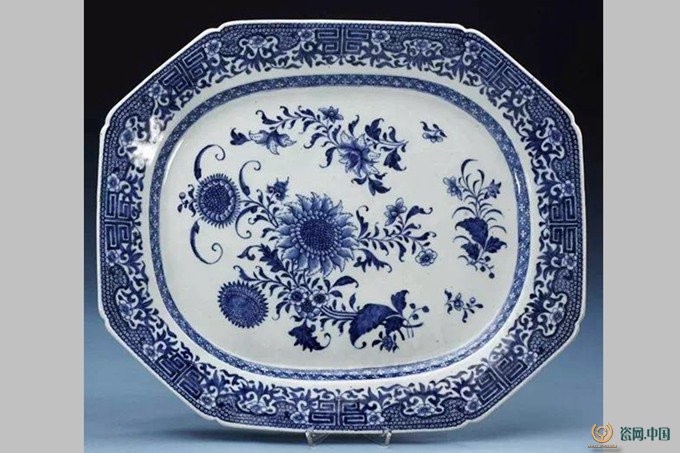
當年和李廣琪一并入道的馬未都和白明等人,如今已成為藝術圈內的名家。而當年,他們都是這個圈子中很執著的一群年輕人。
李廣琪回憶道:“當時勁松舊貨市場的院子里弄了點鐵皮房,一個月,一家二三百塊的租金經營這些舊貨。”30年前的勁松舊貨市場,是為就業放開的謀生市場,并未有規劃,既沒有貨源,也沒有顧客,更無法形成商品價格體系。
70年代末,萬象更新,改革春風讓中國大地開始復蘇,在一些城市出現了一些銷售花鳥、修理鐘表和各種破舊物件的擺攤師傅們。這個時候老百姓可以把各家的破東西比如老木桶、茶葉罐子還有膽瓶等拿出來修理,不要小看這些東西,有很多百姓家中,尤其是修理師傅家中不乏收了百年以上的物件,但是那個時候,普通老百姓連吃飽飯都成問題,哪有心思收藏古玩?百姓當中極少有人有收藏意識,就更別提懂收藏了。但是1987年以后,就不一樣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出現了一些舊貨交換市場,但規模上最大、最活躍的當屬天津的沈陽道“鬼市”。天津沈陽道舊貨市場成型于1987年,經過20多年的發展,由最初的舊物交換市場變成了今天全國聞名的古物交易場所,這就有了后來國內古玩界“先有天津沈陽道,后有北京潘家園”的說法。但是劉新巖強調,那個時候還沒有古玩這種說法,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古玩市場,先是以物換物,最多大家說這是“工藝品”市場。

從1978年到1990年,部分文革查抄物品退賠發放使民間舊貨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古玩市場的形成,是在這種機遇推動下發展起來的,此外,中國古玩市場的發展還離不開國際古玩收藏熱的推動。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留下的寶貝不勝枚舉,國外的收藏家們紛至沓來,搶購這些有價值的藝術品,那個時候有不少港澳藏家來內地淘貨,內地藝術品市場也逐漸被帶動起來。
在中國古玩收藏發展的歷史中,不能不提到北京古玩城,因為它是中國古玩市場形成的一個標桿或者是轉折。1995年,大氣磅礴的北京古玩城正式成立,不但國內外文人雅士、收藏名家頻頻光顧,就連中外使節、商賈政要也成了常客。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國內古玩收藏才從最初的工藝品中分離出來,定格為或者說是細化為真正意義上的“古玩”市場,由此,大大小小的“古玩”城漸漸在全國蔓延開來。直至今日,在全球藝術品市場的各個角落,人們都能夠感受到中國收藏家無處不在的身影。

隨著收藏熱的興起,涌入收藏行業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投身其中,做起了發財暴富的春秋大夢。不但古玩市場如此,可以說整個收藏行業都是一片紅火,參與人數之多前所未有,注入資金之多前所未有,成交價格屢破紀錄前所未有,民間收藏群體也隨之逐漸壯大。全國越來越多的收藏品鑒定宣傳充斥各種媒體,越來越多的一夜暴富奇跡,把人們的欲望一次次地點燃。
對于很多朋友來說,但凡涉獵古玩這個圈子的,沒有人不知道北京潘家園的。那么10年前的北京潘家園又是什么樣子呢?
在潘家園經營了數十年古玩生意的一位藏家回憶,倒退十年,北京潘家園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那個時候,周六、周日清晨四點半就開業,有來自全國20個省市的商販來這里交易,洶涌的人潮達到六七萬人,高峰時多達10萬人,人員涉及各行各業,男女老少都有。當然,這樣的場景也不僅僅限于潘家園舊貨市場,在上海城隍廟古玩市場、成都送仙橋古玩藝術城、鄭州古玩城、武漢文物市場、西安古玩城、合肥城隍廟古玩市場、大連古文化市場、紹興古玩城等全國許多城市的收藏市場里都能看到。該藏家搖搖頭說,現在不行了,那樣的場景不會再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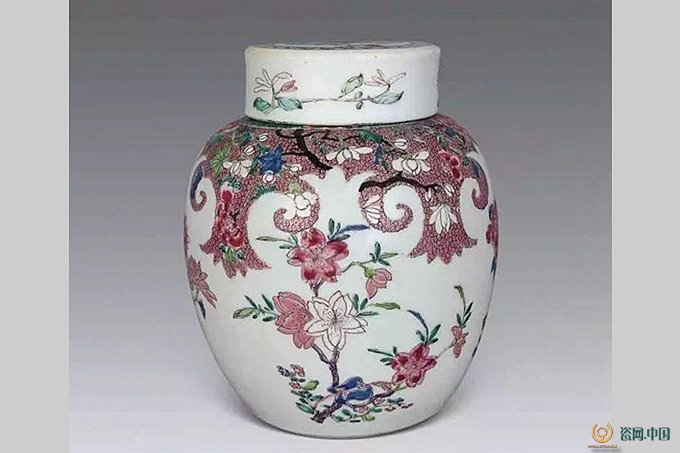
一位在潘家園經營舊瓷器十多年的江西攤主也有同感:“在這個行業中做了這么多年,說沒賺到錢那是騙人的,那個時候每次進貨,家中都會囤不少古玩。”該攤主也毫不諱言,他賣的就是仿古瓷,可是后來,身邊做古玩生意的人越來越多,甚至于,有的人搶不到地攤、商鋪,寧愿花高價從二道販子手中轉租,不知不覺間古玩城也出現了不少。用他的話說,古玩市場就好比一個唱戲的舞臺,真真假假只有自己知道,只要能賺到錢就可以。但是漸漸的生意卻反而不如以前,自己也說不清從什么時候開始,古玩生意越發難做,小地攤上光顧的買家越來越少,尤其是最近幾年,身邊的朋友實力弱的、撐不下去的早已離場。
那么古玩市場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在很多人眼中,這里應該是一個可以淘到古董的地方,行業內習慣稱之為撿漏,也許幾百元淘到的東西可以轉手以幾千元甚至更高的價格出手。

有藏家表示,古玩這一行是名利并存的行業,你有名氣也可,有錢有藏品也可,但最關鍵的還是要有水平,在這個行業中日積月累,方有所成。現在的古玩業界,可以這樣說,沒有接觸幾年古玩就開始經營古玩店的人數不勝數。就像曾經在琉璃廠邊存車的、賣烤白薯的,現在都開了古玩店、字畫店,并且據說生意還不錯。聽起來確實很勵志,但他們根本沒經歷過正規的學習和歷練,更談不上什么經驗,最多身邊有幾個搞古玩的朋友或者自己逛過幾次博物館而已。像這樣的人,手里不可能有真貨。過去無論是經營古玩生意的還是收藏古玩的,只要進入古玩行業就要了解和懂得行內的規矩或習慣,否則就無法真正入這個行。現在不同了,只要愿意,即便手里全是大假貨,去哪里開店、擺攤、展覽、設館等等都沒人攔你,什么行業規矩或誠信統統都靠邊站,剩下的大多都是行業潛規則。幾個月前,就在一年一度的3·15活動中,吉林省金銀寶石飾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免費檢測珠寶玉石時發現,消費者送來檢測的翡翠、蜜蠟中,竟有70%以上是假冒商品。和田玉市場更是讓人眼花繚亂。如今和田玉的造假手段“日新月異”,令收藏者們防不勝防,比如很多玉石利用“易容術”來冒充和田玉等。
潘家園在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份難以言說的情結,在市場中有一些老人,他們就住在潘家園附近,見證了潘家園的興起和衰落,他們曾在這里淘過寶,也曾把自家的老古董拿來碰運氣。張大爺家就在潘家園古玩市場附近,沒事就來市場溜達,偶爾也會把自家收藏的個把物件拿到市場來賣,卻少有購買,用老人家的話說,“古玩市場上的物件真假難辨,自己一般不會輕易買”。

現如今,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淘寶”的神秘感依然存在,可是變化的是,人們對整個市場的信任度。目前的潘家園,多是古玩與大眾工藝品混合經營,在某種程度上,真正稱得上古玩或者具有古玩元素的純古玩物件占的比例并不大。如果一定要在古玩市場里找出一些所謂的古玩物件的話,那么傳統錢幣、陶瓷、玉器、奇石、根藝、票證、像章、琥珀以及各種串珠等算是不少古玩市場最常見的物件。
古玩市場的沒落,讓不少投身其中的小商家們不知何去何從。前段時間,潘家園舊貨市場部分攤主因不滿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有限公司要求簽訂租賃合同的做法引發了沖突。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謂的層層轉租并非一日之問題,其中原因種種且不必多說,但潘家園事件讓不少行內人開始反思,因為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古玩城太多,而潘家園事件只是其中一個縮影而已,曾經的古玩市場創造了多少神話,如今卻這般的沒落。那么古玩市場的出路在哪里?
資深藏家劉新巖無奈地說,搞收藏、玩古玩應是那些有文化底蘊、有雅興、有修養且有閑錢閑空的人的事,而并非所謂的普通大眾之事。以前,潘家園老貨確實很豐富,來到潘家園,有眼力、收藏經驗豐富的藏家確實能淘到寶貝,那個時候,每年出一兩件真品絕對不是謠傳,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潘家園老貨越來越少,換句話說,現在的潘家園就是一個工藝品市場了,而且也少有聽說潘家園再出現一兩件真品了。
劉新巖認為,未來的古玩市場商品和藏品還是要有個明顯的區分,因為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及生活品位的提升,收藏甚至成為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相應的消費比重也逐漸在加大,但是消費者很難辨得清楚哪些是藏品,哪些是商品。就拿收藏石和商品石來說,很明顯后者升值空間并不大。而現實情況是,真正的古玩和商品根本就沒有區分,投機客們以假亂真是所有古玩市場中都存在的問題。古玩,被視作人類文明和歷史的縮影,真正的古玩經歷無數朝代起伏變遷,藏玩之風依然不會衰,甚而更熱。而對一個資深古玩行家而言,信譽的保證必然是賣老貨。
就全國而言,真正稱得上古玩城的也不過15-20家。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在古玩市場發展達到高峰期的時候,不少人懷著投資心態涌入古玩市場,那個時候,古玩城開起來,不少商鋪很快就會被販古商們搶走,所以不但販古的人多了,大大小小的古玩城也開始出現,不管自己原來是做什么的,總之打上個古玩城的名號,就增加了很多神秘感,對不少投資客來講似乎也增加了很多吸引力,而實際上,一個古玩市場里,真正稱得上古玩和古董的物件能達到10%就不錯了。
“前段時間,我去河南、上海和江西等地的古玩市場走了一圈,這些地方的文物市場和北京的現狀是一模一樣,大家叫苦連天,甚至很多市場的經營狀況比北京還要差!”說李廣琪是行內的傳奇人物,還不光是因為他有著“仿古高手”、“鑒定專家”的稱號,其實在中國古玩市場一片蓬勃發展的時候,他在同行業中就有過準確的預判:“七八年前,我就有過這樣的言論,古玩市場會有沒落的一天。那個時候市場非常繁華,行內人不認同,反對我的觀點,現在大家問,為什么會有這樣的預見?”李廣琪的回復很簡單:“因為我對市場的細心觀察,我經營了三十年,我對這個市場的來龍去脈太了解了。”

李廣琪說,將來文物市場和文物商店最少要關掉三分之二,就文物市場而言,中國現有資源有限,截止到目前,已經被開發利用的差不多了。有人說,文物的發掘還可以依靠盜墓和海外搶購。毫無疑問,挖墳掘墓是國家明令禁止的,而海外搶購不太可能。雖說中國已經與世界接軌,但實際上在文物的管理和流通上有很大差別,比如國外一百年以上的文物是不需要交稅的,但是在中國是不可以的,是禁止買賣的。而文革時期遺留下來的文物也基本發掘完了,所以現在面臨的不僅僅是古玩市場倒閉,大部分古玩商店業也會隨之倒閉。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李廣琪認為原因有三。一是,古玩市場混亂,真假古玩充斥市場,因為假貨成本低,很多時候,真貨還賣不過假貨。二是,信息更透明,是影響古玩行業的一個因素。對于很多藏家來說,隨著信息越來越透明,真假貨的辨別不再那么麻煩。以前無論是到日本還是美國,你發現了一個古董 ,因為自己經驗不足怕買到假貨,又不知道該和誰請教,就只能買回后才能找到專家鑒定,但是現在不一樣了,信息透明化,一張圖片、一個電子郵件就可以幫你解決很多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對去偽存真確實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三就是房租貴,對于很多商戶而言,原本市場的沖擊就很大,但是高額的房租加之其他各種原因,導致不少商戶陷入經營困境,無錢交房租,這就致使有些商戶退場,有些商戶慘淡經營。
那以后的古玩市場還會不會好?“真正玩古玩的商家影響不會太大,但是想在這里面撈錢的、想刮點油再跑的這些人都會死得很慘,因為這是一個小眾化的消費群體。”李廣琪信心十足地說,真正的文物價格還會繼續攀高,這是經濟運行的規律,很多東西在不斷完善。過去我們買一個真正的雍正仕女盤,不足兩百美元就能買到,現在2萬美金幾乎都買不到,原因就是,現在是信息時代,通過信息查找,知道這個東西存世量極少,藏家自然會抬高價格,最終,中國的文物市場一定會更加規范。
“面對目前的市場狀況,我和一些同行們也經常討論未來古玩市場的發展方向,以及在經過市場的洗禮后勢必要面臨的問題。比如,各大古玩市場中淘汰的一些貨該怎么處理。”李廣琪說,三年前,他們就在做一個新的計劃,叫“拯救文化市場”。
李廣琪說,首先他們想做像超市一樣的格子鋪。“因為古玩市場內絕大部分貨物隸屬于藝術品,所以我們想在潘家園或者其他古玩城周邊開一個大型的藝術品超市,把商店打造成一個像超市一樣的格子鋪。可能是一千米也可能是兩千米,藝術超市里面可以容納三千個格子或者五千個格子,這樣算來,也就是三、五千個商戶可以進來。我們會先在北京做個示范,一個格子一個月可能是三百元錢,租賃嘛,我們就是讓商戶把煩惱甩出來,我們來做銷售和售后服務。你喜歡藝術品或是想要淘寶,都可到藝術品超市來逛,這里的產品很豐富,一逛就是五百個甚至一千個格子,想討價還價也可以,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服務。待市場成熟后,我們可能也會收取部分傭金,用來作服務、管理支出。”
二是,順應發展趨勢,打造網絡營銷平臺,即藝術品上線。“我們把藝術品交給一些藝術品網站,由網絡平臺在網上進行銷售。銷售的利潤我們一分不要,我們要的是這種模式跟這種宣傳力度。”
三是,季拍或者月拍。比方說,一個柜子五十件貨,就一個號,一百元起拍,因為這里沒有文物,都屬于藝術品的范疇,所以也不會觸犯文物法的相關規定,“這個趨勢一定會有的,這個形式也一定會存在。”
四是,做文化主題。“我們會在北京某一個地方做示范,將來我們會把這種模式推薦給全國各地的古玩市場,我們會把這種管理模式、運營模式甚至于盈利模式都傳給他們,或者我們派人去幫他們建立起一個品牌旗艦店。這次我們去鄭州古玩城考察,現實是百分之八十都是空的,沒人沒貨沒商戶沒客人,全是空的,這樣就是在浪費資源。創建者完全可以把多余的資源搞新的科技和產業開發,實現產業轉型。因為社會在變化,營運模式和商業模式也在轉型,怎么轉,能不能轉得最經濟、最實用、最合理和最有效,這是我們要思考的。相對來說,我們的這種形式最合理最經濟也最實用。”
雖然沒有看到計劃書,但是言談間,能夠感受到李廣琪等古玩界的老行家們肩負的責任以及為了拯救這個行業而投入的熱情。古玩即是一種財富,也是一種文化。而更多的則是承載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玩古玩是在溫習歷史,玩古玩也是在解讀歷史。正確地認知古玩,熟悉地了解歷史,正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一個方向。
(原文標題:古玩江湖:誰在逃生誰又在鳳凰涅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