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26、北宋汝窯 青瓷蓮花式溫碗
十一世紀后半期——十二世紀早期
高10.1-10.5公分口徑15.9-16.2公分 足徑8.1公分 故瓷16929
俯看型如十曲花瓣,口微侈,下接上豐下斂的器腹,立於圈足上,若一朵正在綻放的蓮花。整器滿釉,僅見外底芝麻釘痕五枚,露香灰色胎土。粉青釉色內外一致勻潤,口沿薄釉處見淡淡的粉紅光,釉面密布細碎開片紋,造型靜謐典雅,為陶瓷工藝盡善盡美的代表作。北宋時期除了汝窯燒造有蓮花式溫碗外,舉凡南方景德鎮青白瓷,北方遼境內的定窯白瓷等窯廠皆有之。此種流行亦遠播至位於遼邊境的高麗,傳世品中可見類似院藏蓮花式溫碗的高麗青瓷(圖版27)。
溫碗、注(執壺)及高足臺盞時常成套出現,溫碗徑略大於執壺,因為盛熱水用以溫酒而得名。有關注碗的記錄,文獻上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四十,記錄北宋汴京〈會仙酒樓〉提供客人的飲酒器皿:「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站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碗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雙。」孟元老的記述除了道出溫碗、注及高足臺盞在北宋時期的流行,并說明注子和溫碗并成為注碗,而帶托的盞似為必備品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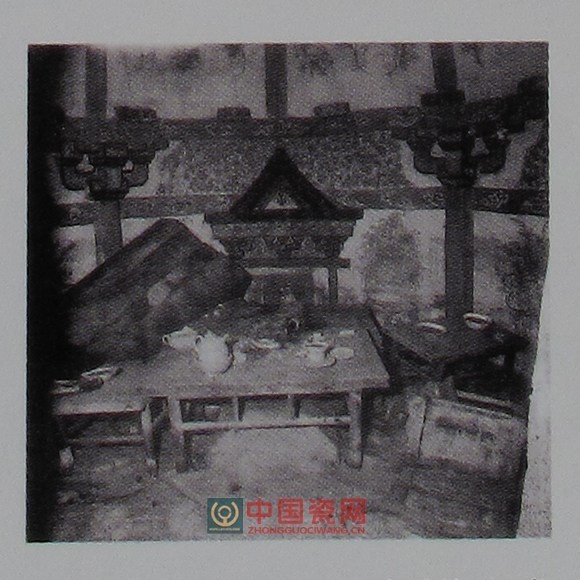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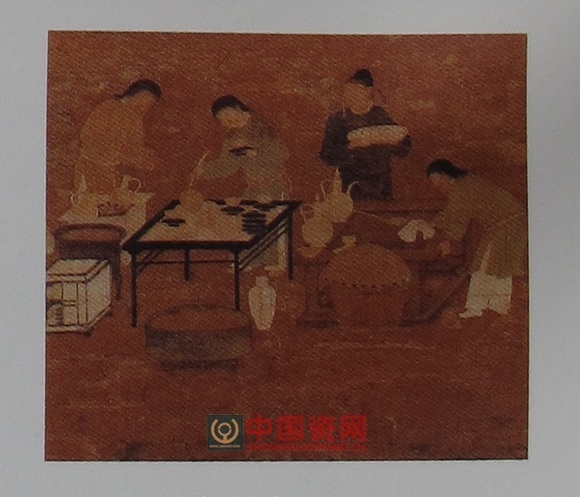
瓷器注碗與臺盞配套出土的例子,可見於陜西彬縣后周顯德五年(958)的馮暉墓,該墓出土一件青瓷灰形器蓋、一件青瓷深腹廣口碗,前者當為執壺的蓋子,后者則是溫碗,同時出土的尚有兩幅青瓷高足臺盞。在北宋圖繪中,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亦以溫碗、注及高足臺盞來描繪兩人對飲時桌上飲品的盛裝器;院藏北宋徽宗所繪的(文會圖)(插圖1),其中描繪文人相聚宴飲及僕從備酒或茶的景象,約及注肩高度的蓮花式溫碗中,置一寬折肩瓜棱形執壺,細長頸上套一長擺的火焰型頂蓋。除了注碗,桌面上尚見大碗、小蝶及高臺盞等宴飲配件。類似此種宴飲器具組合的實景(插圖2),在河北宣化張匡正墓中已發現(改葬於遼大安九年(1093)。其中,墓后室木桌前方的黃釉溫碗中置一造型豐腴瓜棱式執壺、桌面的右方為高足臺盞,左后方的龍首柄碗碗內於出土時尚見鮮潤的紅棗,其它小盤散置於桌面上。此類厚胎低溫的黃釉器常出現於遼墓中,是否為遼地區的陪葬用品,有待日后進一步確認。
目前此種飲器配套的考古出土,多見於(907-1124)境內。如大遼故始平軍節度使韓佚及其妻王氏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此墓出土於1981年北京西郊,乃在遼圣宗統和十五年及二十九年(997、1011)入葬,墓主韓佚為遼的漢族官吏,出土的器物有浙江越窯青釉畫花瓜棱型注子,同出的有劃花溫碗及高8.1公分的瓜式刻劃蜂蜜和草葉紋臺盞一副、碗兩件、碟四件;另外,遼墓中尚有出土於遼寧朝陽耿延毅與耿知新夫婦合葬墓出土的黃釉注及碗,其分為葬於遼圣宗開泰九年(1020)及太平六年(1026)。除了實物的出土,遼墓石室壁畫常繪有備茶或備酒的畫面,其中注碗及臺盞實為主題畫中桌面上的備飲器具;比較著名的壁畫有河南禹縣白沙宋墓一號前室西壁、二號及三號墓西南壁壁畫、河北宣化下八里張世卿遼墓(葬於1116年)后室南壁壁畫的〈備宴圖〉及張恭誘(葬於1117年)的〈宴樂圖〉。遼境內普遍被使用的注碗、盞及壺等器皿,其來源以宋境內用瓷造型如瓜式、花口或圓型器為主。執壺的器型常見短頸、寬肩及有豐腴器腹,其肩高近乎等分器身,并有長頸,如(文會圖)中的執壺類型。
薄胎的花式溫碗,以北宋中期瓷都景德鎮附近出土的影青瓷為多。而溫碗常與臺盞配套出現,器型亦類似院藏(文會圖)中所見(插圖3)。此類如院藏坐於高足上的蓮花式溫碗,造型雅致,有若半開的蓮花或郁金香,為唐宋以來陶瓷仿金銀器造型的一種流星標記。由考古出土的花式溫碗所配的執壺類型來看,執壺的器身高度常及溫碗的口沿,細長的頸上設一長擺的蓋子,并以坐獅為蓋頂,皆此以平衡寬肩、細頸的執壺造型比重,并營造一種另類造型的趣味性。除了以上所謂的執壺類型,蓮花式溫碗亦常配有瓜式執壺,如東洋陶瓷館藏的韓國青瓷瓜形水注(圖版29),遼境內亦出土定窯系白瓷蓮花式溫碗及葫蘆型執壺。由此可見北宋時期蓮花式溫碗所配的執壺樣式甚多,而非定於一。院藏的汝窯蓮花式溫碗雖無注子的配套出現,但由英國大衛德基金會藏有花口汝窯青瓷盞托(圖版21)及清涼寺窯址汝窯盞托(圖版22)的出土,或可想見此溫碗的配套情形!(陳玉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