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位作家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任何民族的文化,無論在歷史上有多么輝煌,倘若后無繼者,便只是一片斑斕而沉默的史跡而已,只有后人永遠珍愛它,并發揚光大,才能使古代文明轉化為現代文明。”
三句話不離本行。筆者在陶瓷藝術界工作了近50個春秋,造型、裝飾無不涉及,然而我對刻瓷這門藝術,由偶然愛好到外交部禮賓司“訂貨”,后來就有了一種出奇的愛好和癡迷的追求。30多歲那幾年,忘記下班,廠門被鎖,翻墻而出的狼狽相常有。本來這些瑣事不去回憶它也罷,但前些年見諸報載的事實不時入目。后來真的自責起來:敝人是屬于給點陽光就燦爛的那一族。
同行的朋友都說淄博的刻瓷藝術是成功的,是有幸的;業內人士也坦言,世界刻瓷在中國,中國刻瓷在淄博,其實一點也不虛假。我實話實說,在淄博刻瓷藝術這片花圃里,所幸有一群活潑、健康、睿智、勤勞的蜜蜂,是它們吸允著甘甜的露滴,傳播著成果的花粉……
人近“從心所欲”之年,思維的輸入與輸出已不能成正比了,追憶與比較不斷閃現。我在國營瓷廠的46年中,有幸結識了著名國畫家李左泉先生,他也就職于該廠畫陶瓷、國畫,他的國畫雪景為“諸家之冠”,“炎夏觀之,使人無酷暑之感”。先生之畫風至今尚無人敢追及。1958年,我受廠方指派,與左泉先生同住一舍(14平方米,兩床),任務是提水,打飯,看爐子(取暖)。耳濡目染先生打夜作、賞雨、賞雪的生活規律,因此,我也就成了未經廠方簽訂正式師徒合同的學生之一。當時,青澀懵懂的少年怎能去理解“學前人不泥古法,創新獨辟蹊徑”的哲理。就是這樣一位全國著名畫家、山東省第三屆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淄博市第三屆政協委員,一夜之間,淪為“反動權威”、“牛鬼蛇神”,于1968年12月31日含冤辭世。正式的、非正式的學生們無一耳聞噩耗,直至11年后的1979年4月7日上午,由黨組織出面,在淄博瓷廠大禮堂為左泉先生召開追悼大會,平反昭雪。
物換星移,時光飛逝。1981年5月,我經過層層考核、選拔,帶著刻瓷工具,第一個踏入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傳播中國的民族藝術。在十幾個小時的飛行中難能人睡,思緒萬千……記得在科隆的一位臺灣藝術家風趣地說:“你到德國來,家庭可有‘背景’?”
再后來,我當選了山東省第六、七、八屆人大代表。翻閱當年那一本本日記和那一張張發黃的報紙,它不僅折射了一個人的人生道路,也真實地印證了一段歷史軌跡,我更想到了李左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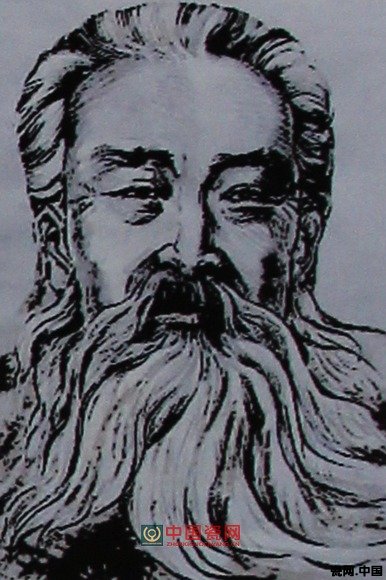
圖1、為李左泉先生畫像
我沒有仔細統計過刻瓷隊伍的人員數字,也沒有深究這50年的時間概念,重溫“報集”關于刻瓷群體的文庫,又找到了理論根據和知識升華。
當今,刻瓷園地滿目珠璣。以淄博為放射點,與全國、與世界溝通的放射線密度越來越大。人文情懷、藝術造詣逐年突顯,僅在淄博,榮獲“中國陶瓷藝術大師”稱號的有6名,山東省陶瓷藝術大師44名,山東省杰出青年陶瓷藝術家20名,一批青年陶藝家如雨后春筍,形成讓人寬心的金字塔。更讓人驚嘆的是:不少職業學院意識超前,膽識過人,請藝術家上講臺(如紡織、絲綢學院),這是一群不可低估的希望之星,是陶瓷文化的后備軍。
筆者作為中國陶協刻瓷文化研究會會長,雖然是階段性、過渡性,但也有不少學問和課題等待去破譯,就像中國的書法,不同的人寫上去,就是兩個世界,“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一粒種子,只要有了適合它的土壤、水分;一棵嫩芽,只要它接受陽光;一株鮮花,只要它與蜜蜂交友。中國的刻瓷藝術,從明末清初延續到淄博復蘇,已過“而立”之年,它將攜手50歲的兄長,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一起幻想、繁茂,一起成熟、深思。在這經濟大潮中,新的、好的陶瓷藝術精品不斷問世,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向我們的先人回應著同一個聲音——“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
刊登于《淄博日報》
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