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圖3可以清楚地看出,唐鈞藍斑釉與宋元鈞窯系釉一樣都具有細分散的液滴狀分相結構,其分相液滴的直徑大都在60~120納米的范圍內,符合瑞利(Rayleigh)散射定律(散射光的強度與波長的四次方成反比)設定的先決條件,因此釉層內近似球形的液滴能夠將入射光中波長較短的藍色光波散射出來,使釉層呈現出美麗的藍色乳光。從圖3中還可以看出,唐鈞釉的滴狀相和連續相內部都發生了明顯的二次分相現象,但這些第二次分離出來的滴狀相的尺寸極小,大約只有10-15納米,對光散射和呈色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對下白峪唐鈞藍斑釉的直接透射電子顯微鏡觀察也得到了與上述結果類似的結果,其DTEM照像見圖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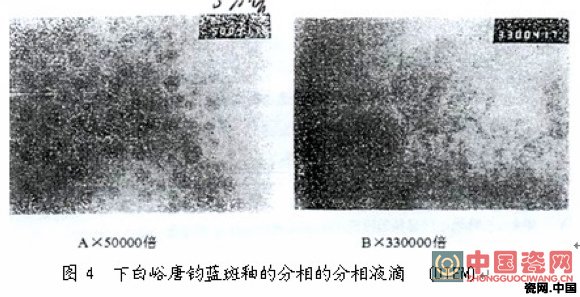
圖4 下白峪唐鈞藍斑釉的分相的分相液滴 (DTEM)
(4)結語
由此可以得出:
(一)、從本質上看,唐鈞釉和宋鈞釉都是具有相同化學組成特點和細分散的液滴狀分相結構的分相乳光釉,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兩類釉”。其差別不過是所用的工藝方法不同,是非本質性的。
(二)、唐鈞的月白色面釉及其在黑底釉上形成的乳光窯變藍斑是世界陶瓷史上有實物為證的第一個分相乳光釉。繼唐鈞之后在同一窯區陸續燒制成功的柴窯、鈞窯和汝窯的“雨過天青”等一系列分相乳光釉,都是在唐鈞的啟示下發展演變出來的創新釉種。前者是源,后者是流。
(三)、唐鈞器上的乳光藍斑只可能是后世藍鈞釉等分相乳光釉的先導,而不可能為鈞窯釉上的紫紅斑“開啟先聲”[12]。這種紫紅斑應是先人看到當時白釉器上常見的銅綠斑偶爾受還原作用變成銅紅斑這一現象受啟發而發明的。因為自唐以來,包括鈞瓷發祥地在內的許多河南省的古代窯場中燒造的白釉器上常以銅綠斑作裝飾,這種銅綠斑受還原作用變成銅紅斑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可以想見,這一發現不但直接引致了北宋早期或中期天青乳光釉上紫紅斑的發明,也進而啟發人們將少量燒制銅綠斑的釉料摻入藍鈞釉中,從而使鈞臺窯中紫紅背景釉色上散布乳光藍色兔絲紋或蚯蚓走泥紋的銅紫紅窯變釉的研發成功成為可能。至此,對鈞臺窯舉世聞名的兩項偉大發現——分相乳光藍釉(藍鈞)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銅紫紅窯變釉,便告完成。
參考文獻
1、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13
2、陳瀏,《陶雅》卷下: 51
3、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60
4、同2:1
5、葉喆民,河南省禹縣古窯址調查記略,《文物》,(1964)[8]:27-36
6、馮先銘,河南省汝縣宋代汝窯遺址的調查,同上:15-26
7、趙青云,河南禹縣鈞臺窯遺址的發掘,《文物》,(1975)[9]:57-63
8、蔣玄怡,《吉州窯》,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9、加藤悅三,《釉調合の基本》,(1975)
10、劉凱民,鈞窯釉的進一步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239-241
11、陳顯求等,唐代花瓷的結構分析研究,硅酸鹽通報(1986)[6]6-11
12、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