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仿古小組后,我們開始模仿和參照一些古代青瓷的造型,根據專家提供的古瓷釉配方的實驗數據,進行拉坯、裝飾、施釉和燒制。李懷德師傅第一次叫我干的活是修一把木瓜壺口沿上面的一條棱線,很細小很精細的那種線。以前我是做粗瓷碗的,粗瓷碗不需要很精細的裝飾線,所以木瓜壺口沿上的線我一直都修不好。于是,我對師傅說,這個太難了。師傅說,你現在做的是仿古瓷器,不同于做粗瓷碗,你要把心靜下來,要小心翼翼的,馬虎不得。師傅很嚴厲也很耐心地批評了我。從那時起,我在師傅的指點下,知道仿古青瓷不同于普通的粗邊瓷碗,這是做精品,不是放“衛星”,要心細,要把心沉下來,不能毛糙。那時候廠子里的條件很苦,碾磨、配料、拉坯、上釉、燒制,每道工序我們都得先給師傅做下手,仔細揣摩,細心領會,不然,怎么能學到真本領。經過幾年的磨煉,我在師傅的指導下,基本掌握了仿古青瓷的各種工藝和技術。有次去北京參觀學習,在故宮博物院里,我第一次見到了傳世的南宋時期的青瓷珍品,使我大開眼界,真正的古瓷珍品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真嘆服古人的精湛技藝和燒制技術。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做出像古人那樣的青瓷藝術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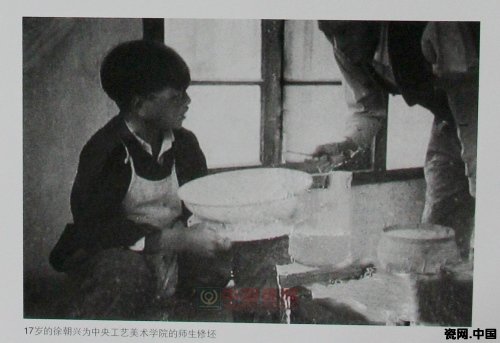
17歲的徐朝興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師生修坯
我們做仿古青瓷的時候,國家輕工業部的李國楨高級工程師,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梅健鷹教授,浙江美術學院的鄧白教授,浙江省輕工業廳的勞法盛、葉宏明副總工程師等都先后來龍泉幫助我們做仿古青瓷。那是非常好的機會,當時我經常向他們請教問題,學習技術知識,知道了許多有關龍泉青瓷的奧妙。龍泉青瓷真是了不起,怪不得這些大專家都來這里搞研究、搞考古、搞鑒定。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為了破解古代青瓷燒制工藝和技術,省考古研究所的專家還對大窯、溪口、金村等古窯址進行了深入地挖掘,采集古代青瓷殘片、殘器作為標本供研究單位使用。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化工研究所、輕工業部硅酸鹽研究所等國家科研單位,對青瓷考古標本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研究古代青瓷的胎、釉構成的原料成分和相關數據。我們龍泉瓷廠的仿古小組,就根據專家分析出來的胎、釉成分與數據進行仿制和試驗。1959年我們完成了制作建國10周年人民大會堂用瓷的任務,特別是以《鳳耳牡丹瓶》為代表的一批仿古青瓷產品,使幾乎失傳了近三百年的龍泉青瓷得以延續。1960年,仿古小組仿制青瓷的新成果和新工藝不斷,像青白瓷結合釉、青瓷堆花、青瓷開光、青瓷點彩、哥釉仿制和大件花瓶等,都是那兩年搞成的,這些新產品胎質細膩、釉色穩定,仿制工藝和技術也接近古瓷,受到了專家的好評。在仿古小組的四五年里,我虛心向師傅學習,學會了龍泉青瓷傳統燒造技藝的一整套工序,包括配方、拉坯、修花、燒成等,還幫助浙江美術學院的老師和學生們燒制作品,像李松柴、陳淞賢,當時我都幫他們燒制過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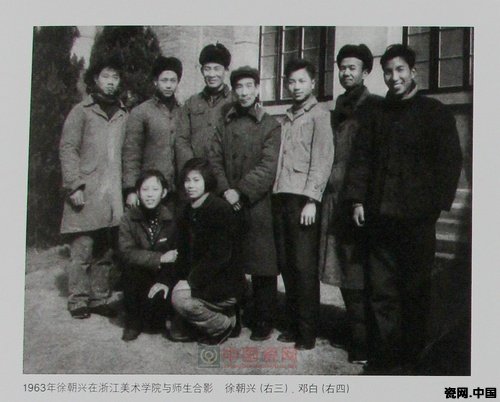
1963年徐朝興在浙江美術學院與師生合影 徐朝興(右三)、鄧白(右四)
本來有一個很好的機遇,我是可以在大學當教師的。那是1963年,浙江美術學院陶瓷系為配合畢業生實踐教學,建了一座倒煙窯為學生燒制陶瓷,需要一個掌握制陶技術的工人去做教學輔導,于是就把我從龍泉借調到美院。當時陳凇賢教授還是學生,他們班里總共有6個學生,平時設計的作品都由我試燒。我和他們班同學相處得非常好,現在我和陳淞賢還經常來往,他現在已經是美院的名教授了。我本來是做幾天就要走的,可是美院教學需要懂得燒制技術的工人,就索性把我留下沒讓我走。我當時思想很先進,是共青團員,在美院里參加教師的團支部組織生活,到教師食堂去吃飯,享受的是老師的待遇,美院沒把我當外人。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沒有東西吃,在教師食堂吃飯,營養比較好,本來我個子是很矮的,那時我突然長得很快,我的個子幾乎全是那年長的。在美院里,我還有一個好機會,就是可以隨時請教老師,學習陶瓷專業理論,尤其是那些學生,與我的年齡相仿,可以非常隨意地進行交流。記得我還和他們研究和試燒過官窯的產品,美院的老師都很欣賞。四個月后,美院要把我留下來當正式技術工人,專門做教學輔助工作。可不巧,我原來有一個師兄,是在仿古小組一起跟李懷德師傅學藝的,因為吃不了苦就跑回福建去了。就因為這樣,我們廠的技術科長就到美院把我叫了回去。當時我家庭成分不好,領導叫我往東我是不敢往西的,如果我堅持一下是可以留在美院的,但我還是乖乖地跟他們回了龍泉。后來還有一次機會也可以離開龍泉,結果也沒有走成。那是輕工業部高級工藝師李國楨在龍泉搞釉配方實驗,我給他當助手協助他搞釉配方工作,我工作積極認真。他覺得我有深造的前途,就想把我調到北京,廠里還是不肯。我年輕時兩次離開龍泉的機會就這樣失去了。
我從美院回來后還是在仿古小組工作。50年代末,我發現青瓷制作先做模型。然后素燒,完了再翻石膏模型,不僅費時、工序復雜,而且成功率低。我就想能不能直接用石膏做模母呢?那時我沒有專門的時間做技術試驗,只能利用下工后的業余時間,因為當時我還是學徒,我幾乎用了三四個月的工余時間進行試驗,有時是連續幾個晝夜不眠不休的,最后終于試驗成功了。用石膏直接制作模母的新工藝在當時的龍泉制作行業是一種技術革新,要知道原先的老模母工藝已經延續幾百年了,這顯然是個突破。我雖然在仿古小組是學徒工,但我在技術也日漸成熟起來,對仿古瓷的燒制和制作也越來越成熟,并暗下決心要做出超越南宋龍泉青瓷水平的仿古青瓷。
令人惋惜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仿制傳統龍泉青瓷的工作被扣上了“封資修”的罪名,廠里不能再生產仿古青瓷的工藝品,只能生產民間日常用的瓷器產品。因為我出身不好,廠里不讓我在仿古小組,讓我去基層干粗活,哪個人沒來上工我就去哪個地方頂替,什么雜活都得干。不過,干什么我都用心地學,學到了更多的東西,現在回想起來,雖然不后悔,但當時真的很委屈。暗地里,我還是非常鐘愛仿古青瓷,偷偷地潛心研究自己的青瓷制作工藝。有意思的是,我是“三進三出”仿古小組,運動一來,我就被轟下車間去干粗活,運動一過,我又調回來做青瓷,幾番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我也習慣了。當時龍泉瓷廠有好幾個分廠,總廠下一個命令,我們就得做一樣產品,如茶杯、酒具、大碗等等,包括那些鐵路列車上使用的水杯,“文革”時印有毛主席語錄的杯。那個時候基本上是批量化的東西,個性化的東西是沒有的。70年代初,周總理給了龍泉青瓷起死回生的機會。那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周總理主持歡迎國宴,外交部特意指定將龍泉青瓷作為國宴專用餐具。當時還為此專門發過批文,日期剛好是1月18日,廠里神秘得很,把生產這批青瓷餐具叫做“118工程”,我也參加了研制和生產這批青瓷餐具。這批以“云鶴”圖案為主的餐具是當時龍泉青瓷生產的最高水平,而那時龍泉青瓷圖案一貫都是以金魚、熊貓、牡丹、梅花為主,以免被人打上“封資修”的罪名。
總的來說,在仿古小組也好,在車間干粗活也好,在美院當教師也好,從“大躍進”到“文革”時期的人生經歷,對我來說,雖坎坷曲折,但至今仍有很好的教益,我很珍惜。

